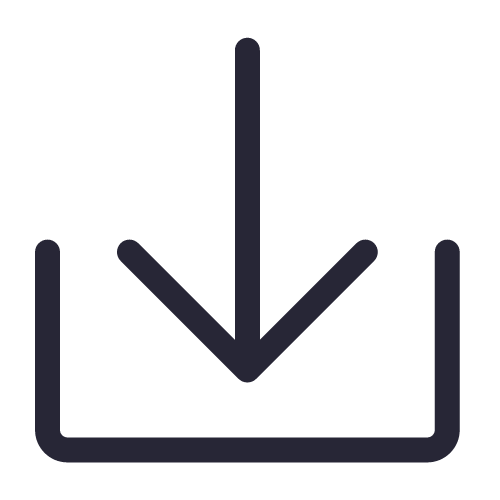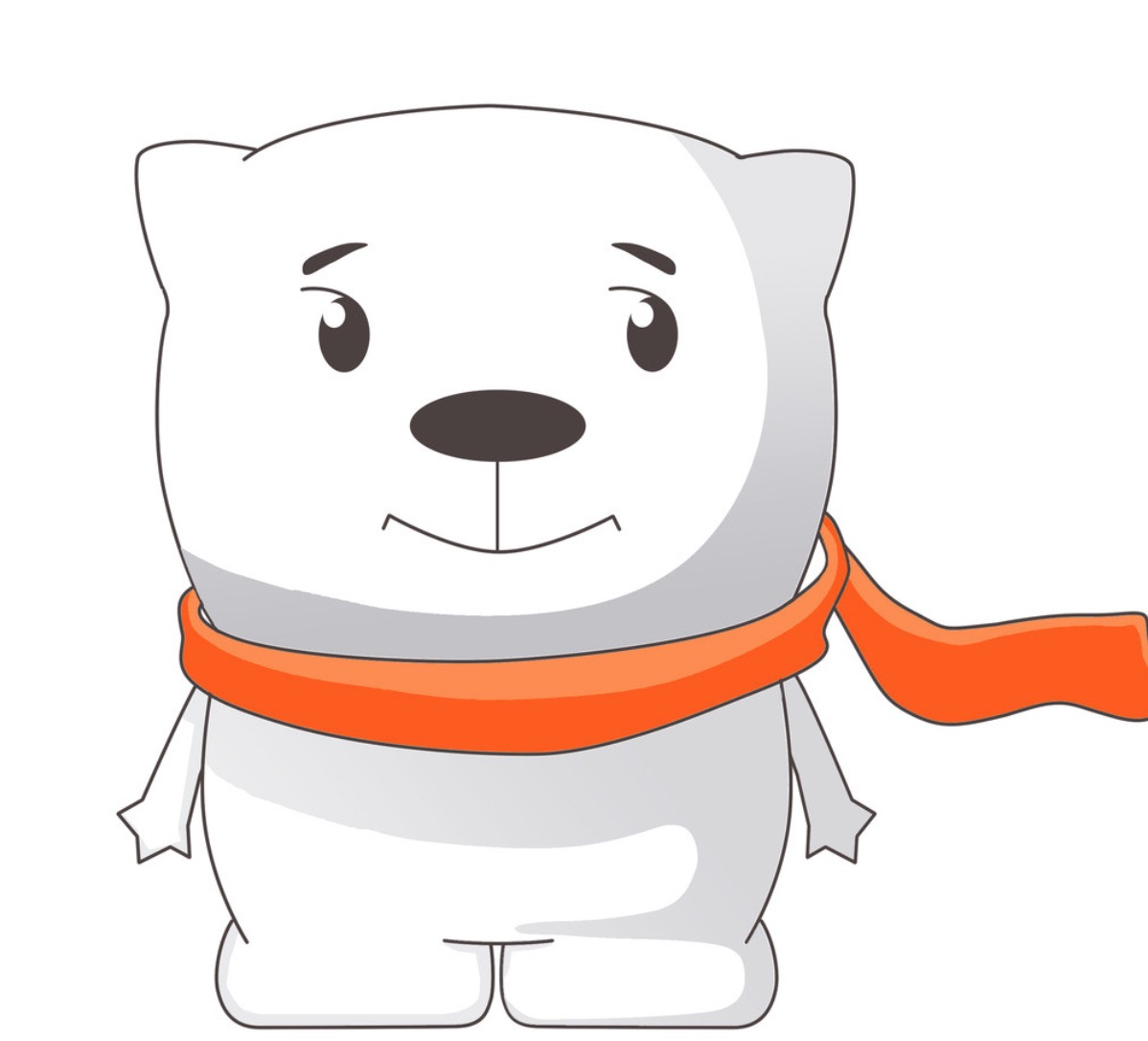在理论法学研究的材料中,特别是法史这块,部分学者认为素材有位差之分,档案资料、传世法典、正史、方志等传统使用的基本材料居于核心地位,文学作品应当处于较为次要的地位
诚然,像小说、戏剧、寓言等题材的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虚构成分,甚至会对现实生活进行扭曲化、夸大化
但正如学者徐忠明所说的,“无论是历史叙述还是文学作品,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也许都仅仅是文本资料罢了,它们之间并无高低优劣可言……关键要看历史学家用以研究什么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吾认为手段可以多种多样,丰富化的形式都蕴含着一个“终极目的”即研究主旨
材料间的相互佐证,史料与文学间的相融,既拓宽了传统的研究视野,也加强了论证的说服力
一方面,西方后现代性思潮打破了传统研究格局,带来了蔚然成风的“求新”、“求异”热浪,加速了跨学科间的融合
另一方面,在追求覆盖面、宽领域的同时,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深度有所受限
法律与文学的联姻正是在如此大环境撮合下结成的
广义上的法律说抽象可以很模糊,说具体可以很清晰,就本质而言,无非就是一纸文本
它可以是立法者的制定法文本,可以是当事人的协议文本
从这个角度来看,兴许法律文本和文学创作的文本有某种类似的牵连、共通之处,只不过前者具备国家保障的强制力,后者拘束力有限
为了避免机械套用此种客观性,笔者将从冯梦龙编着的《醒世恒言》中的故事为切入点,分析、比较文本话语权的异同之处
一、古时户婚案中“妄冒为婚”的问题 常言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们自小就被灌输、知晓这样一个道理:我国封建时期包办婚、买卖婚的现象严重存在
在感慨自由婚姻的可贵之处时,我们是否会有以下的困惑或疑问:达到什么样程度的要件会使婚姻成立生效,受到国家礼法的保护?新郎新娘连面都没见过,是否有骗婚的可能性?国家会不会去干涉、调整婚姻欺诈的局面?婚姻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要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庆幸的是,我们不仅可以从相关典籍记载的司法案牍中一窥究竟,还可以从分散于文学作品各处的零星的司法事例汲取直观感受
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选取了《醒世恒言》里的两个事例:“钱秀才错占凤凰俦”(案例一,简称钱秀才案)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案例二,简称鸳鸯谱案)
案例一的故事梗概如下,洞庭西山有一富商叫高赞,他为了给美貌聪明的女儿秋芳找个才貌兼全的君子,向社会广发“招婿帖”--附加见面考核的条件
苏州府吴江县有一穷酸秀才叫钱青,相貌清秀,博览群书,寄居在表哥颜俊家中
颜俊家境殷实,却面相不佳,文采欠缺
颜家这位大少爷道听途说地喜欢上未曾谋面的高家“白富美”,央求远亲尤辰上门提亲
为了这门婚事能够成立,颜俊和尤辰撺掇着让钱青冒名顶替去奔赴面试
高家上下对钱青的气质、学识谈吐甚为满意,择日收下了颜家的聘礼
到了亲迎吉日的那天,颜俊担忧自己的相貌会露馅,将计就计地让钱青去把新娘接回来
意料之外的是,江河风云突变,高家为了避免吉时的拖延,让钱青当场举行了婚礼,三天后天气转好才返回
钱青在这三晚安分守己,不曾碰过新娘子;但颜俊却认定钱青不老实,坏了规矩,一等钱青上岸,就把他揍个半死,冒名替婚之事也随之败露
知县路过,审理了此案
案例二的情节大致如下,杭州府刘秉义育有一对子女,分别安排了他俩的婚事:儿子刘璞,已聘下了孙寡妇的女儿珠姨为妻;女儿慧娘,待兄长完婚后嫁给裴九的儿子裴政
不料刘璞在即将迎娶珠姨时,抱病在床
刘家当机立断地隐瞒其病情,决意要儿子娶妻冲喜
孙寡妇听到了相关的流言蜚语,不能让女儿珠姨误了终身,让儿子孙润男扮女装前往刘宅,替姊完婚
刘家公婆担忧刚过门的媳妇寂寞,让慧娘去陪寝伺候,结果孙润和慧娘擦出了爱的火花
当刘璞康复后,真相逐渐明了
裴九知道后要求刘家退还彩礼,而刘家也跑去衙门状告孙寡妇
杭州知府乔太守问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最终判定孙润与慧娘为妻,刘璞仍与珠姨成亲,同时擅自作主将孙润的未婚妻配与裴政
两案中都存有婚姻当事人被调包的情形:钱秀才案是男方冒名变更主体,希冀以狸猫换太子的形式娶回新娘;而鸳鸯谱案则是女方冒名变更主体,试图以拖延时限的方式观察新郎的病情
不可否认,两案中冒名的动机各有不同,处理的结果也略有差异
但是,我们所要思索的关键点在于,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民事纠纷会不会实际存在于当时的社会生活?是普遍性还是特殊性的反馈?假若大相径庭的话,原因又会出现在哪?据此,笔者查阅了相关典籍,发现历代传世法典(如《唐律疏议》、《大清现行刑律》等)皆有直接针对“妄冒为婚”的条文
也就是说此类民事案件实实在在出现过,而且数量也确实纷扰繁杂
说到底,婚姻是人伦之始,伦理秩序从婚姻缔结开始
假如连起始之处都混沌无序、不闻不问,庞然大物般的礼法系统也就难以牢固控制社会
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婚姻不是一纸文凭所能决定的,往往会牵涉到两个家族的结合
受到传统宗法制的影响,配偶身份的不同,会导致继承的内容不同,比如田宅等财产、债权债务关系和社会地位
再者,受女性贞洁观念的约束,一旦“妄冒为婚”水到渠成时,女方想要解除婚姻关系就承受沉重的压力,继而勉强维持旧婚姻
因而封建礼法也就会用专门法条调整“妄冒为婚”的情形
细察上述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共通之处:媒人的辅助作用
从形式上来看,“妄冒为婚”是出于共谋的故意,媒人是共犯,是帮助犯
从责任上来看,媒人往往会严惩不贷,审判官对其行为做出否定性评价
从原因上来看,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媒人对相关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对正确信息自主地加以过滤
总而言之,我国封建社会的“妄冒为婚”现象存在着普遍性的社会原因,而此种社会原因又根深蒂固、不易瓦解撼动
婚姻之要义岂能建立在欺诈、妄冒的基础上?故律法的明文规定既有威慑教化之力,也为案件的特殊性留有自由裁量空间
二、古时律令条例对“妄冒为婚”的规定 对于“妄冒为婚”的规定,可以追溯到唐律的“为婚而妄冒”专条
该条规定如下,“诸为婚而女家妄冒者,徒一年
男家妄冒,加一等
未成者,依本约;已成者,离之”
《唐律疏议》曰:“为婚之法,必有行媒,男女、嫡庶、长幼,当时理有契约……‘未成者依本约’,谓依初许婚契约
已成者,离之
违约之中,理有多种,或以尊卑、或以大小之类皆是
”本条文主要惩治既定婚约的违反,为“妄冒为婚”的行为奠定了立法基础
婚姻大事理应有契约,正如案例二中的裴九和刘家是已经有白纸黑字物证般的婚约在手
未过门的媳妇慧娘私自与孙润产生爱慕之意,着实给裴家打了个振聋发聩的耳光
此类有损家风的名誉声望一旦告上法庭,那可是有理也说不清,除非拿出婚契作为证据
兴许唐律仅仅开创了“妄冒为婚”的立法先河,有些规定还比较模糊、不统一
而《大明律》的“男女婚姻”条则具体解释了男女两家各自的妄冒情节:“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疾残、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
……若为婚而女家妄冒者,杖八十
谓如女有残疾,却令姊妹妄冒相见,后却以残疾女成婚之类
追还财礼
男家妄冒者,加一等
谓如与亲男定婚,却与义男成婚,又如男有残疾,却令弟兄妄冒相见,后却以残疾男成婚之类,不追财礼;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
” 为了给法律概念下定义,立法技术上采用了列举式和概括式这两种通常的方法
《大明律》用列举式的方法阐释了“疾残、老幼、庶出、过房、乞养”等情形不得妄冒,婚书决定各方的法律责任
替亲人去相亲的做法是律例明文规定禁止、不可取的
案例一中的钱秀才正是轻率地做出了替表哥颜俊相亲的决定
假若不是天有不测风云的情节安排,颜俊则生米煮成熟饭地规避了法律
文学作品中常会出现替亲人去从事某种活动,诸如花木兰替父从军、缇萦上书愿为婢来代父赎罪等等
我们可以看出血浓于水的亲情维系着一个家族、一个时代
法律并不是对此类情谊行为一味无情地封杀,只是一旦“妄冒为婚”的纠纷急剧增多了,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虚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文学作品倾向于大团圆式的美好结局,以飨读者
一般而言,文学较为讲究新颖性与创造性,法律则更注重连贯性与稳定性
事实上,《大清律例》继承了明律关于“妄冒为婚”的成文律法,其“妄冒为婚”条规定:若为婚而女家妄冒者,杖八十,追还财礼;男家妄冒者,加一等,不追财礼
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离异
从律条的字面意思来看,可以大致推定“妄冒为婚”的构成要件:其一,婚约在手;其二,冒充、隐瞒身体缺陷和年龄等事实的欺诈行为;其三,事后败露不予以追认
妄冒一方的主婚人(媒人)和作为婚姻当事人的男女双方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男女婚姻的效力方面,从唐代开始直到明清,法律分别不同情况,或否认或肯定原定婚姻的效力,其标准主要是尊重无过错方(非妄冒方的主婚人和婚姻当事人)的意愿
”无过错方一般对婚姻缔结的默认许可,主要是对妄冒者的同意与承认
因而,假若无过错方不认可,那么与被妄冒者的婚姻自始即不成立,已成婚者强制解除婚姻乃合情合理
另一方面,在妄冒者之间也许会出现两个无过错方的情形,既然两者皆无过错,那么按照无过错者的意愿是作不出决定的,而是按照婚姻成立时间的先后决定婚姻的效力
因此也就是律例条文所表达的相关内容:如妄冒者未婚且并无婚约在先,则与婚姻无过错方成立婚姻关系;反之,则否认二者之间的婚姻关系
如此看来,明清两朝“妄冒为婚”条关于婚姻关系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和处罚做到了天理、国法、人情的相交融
在文学作品中描述妄冒为婚的内容,虽说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加强了律例条文的法制宣传,让老百姓知道这样子做是违法的、不可行的,但是更主要的表达了诚信婚姻的一种礼治秩序
古时婚姻是“礼”的一种缩影,“礼”是法之理义、法之精髓,故而“妄冒为婚”在中国传统社会有其特殊性
我国古时长期处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人口流动性差,地域性较强
婚姻缔结往往局限于本乡本土,中介媒妁传递的信息也就显得很关键
婚姻应建立在诚信为本的礼义教化基础上,否则会受到正式律法的追究
三、司法官员对“妄冒为婚”的处理 通过文学性的故事文本,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此类“妄冒为婚”纠纷的解决方式
在案例一的钱秀才案中,小说中的司法官员审理如下:首先,吴江知县讯问了当事人,对尤辰这一中介方进行了拷讯
然后知县请来“稳婆”以验明新娘正身
其次,主审官征求了受害方高家的意见,追问高赞愿意把女儿许配给谁
最后,知县作出判决:“……高氏断归钱青,不须另作花烛
颜俊既不合设骗局于前,又不合奋老拳于后
事已不谐,姑免罪责
所费聘仪,合助钱青,以赎一击之罪
尤辰往来骗诱,实启衅端,重惩示儆
”并将尤辰重责三十大板
按照前文提及的《大明律》和《大清律》的规定,如果“妄冒为婚”,会有两种不同的后果,即“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
”这里的“仍依原定”是指“男女俱归原相见之人也”
另查《大清律》“男女婚姻”的注释:“如妄冒相见男女,先已聘许他人,或已经配有室家者,不在仍依原定之限
”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情法两尽”的裁判结果
譬如,审判官对媒人的骗诱行为深恶痛绝,给予其重罚
尽管我们不能草率地预设以下前提:文学想象是建立在司法实践的空间上,但是文学想象也许与司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层层递进的契合相关性
在“鸳鸯谱”案中,作为官府理想代表的乔太守,通情达理,并恰当利用官府的权威,作出了三对新人喜结连理的判决,从而将“妄冒为婚”的故事喜剧结局推向了最高潮
单就小说中的那份脍炙人口的判词来看,与现今格式完整的司法判决极为不同
这样一份“息词”更蕴含着调处息讼的目的
因为双方当事人“俱各甘伏”,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的妥协,进而产生法律约束力
四、结语 明清律学家在妄冒为婚是否会与无效婚姻相挂钩的问题上,存在着不一样的解释
这两方面的观点分别是:第一种观点认为妄冒者婚姻关系不成立,因为在其适用条款时主张严格按照现行的律例条文解释
例如沈之奇即认为:“已成婚者,离异,不得因已成婚,即听完聚,而遂奸伪之愿也
” 在这里有“离异”的法律规定,原因有二:一方面不合适、不恰当的婚姻要从源头上纠正错误;另一方面阻止妄冒者合法地对受骗者继续实施侵害
离异可以摆脱这种不情不愿的婚姻状态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否离异取决于女方真实的内在意思,如果女方不愿“离异”,那么就应该继续合法地维持这一婚姻关系的存续
例如《大清律集解附例》即将该条律文注解为:“已成婚者离异,女别嫁,男别娶;若女子不愿别嫁,亦应免其离异”,“女虽妄冒,其男犹可再娶;男若妄冒,其女遂致失身,故加等也
” 在当下学潮流派中,关于文学中的法律,苏力学者认为文学作为研究材料的价值,并不在于“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本身是否真实发生过,而是事物显示出来的逻辑关系和普遍意义”
总体而言,苏力倾向于认为,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应该从文学作品中发现和提取与当前中国法治转型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而从法理学和法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解释,以期建立有关法律问题的新理解
文学一直承载着重大的正统法律意识的传播和整合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具有了某种社会控制的作用
最后,我们可以借鉴“新文化史学”的方法,通过检视有关法律问题的文学想象和文学表达,来解读其中蕴涵的法律文化的丰富内涵,探究某一时代法律文化的精神状态
当然,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判决书中的体现
审判官既然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文人墨客担当,通过诗性裁判,使得司法同大众紧密联系
它充分体现了法律的终极目的是在于实现社会的高度和谐
这是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应有的尺度,也算是我们独有的“特色”